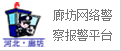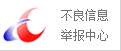【內(nèi)容摘要】 “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及《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商標(biāo)授權(quán)確權(quán)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明確了姓名權(quán)可以成為商標(biāo)法中的在先權(quán)利,但卻是以保護姓名權(quán)為名,行保護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之實。此種名實不副的狀況必然導(dǎo)致一系列法律適用問題,需要根據(jù)現(xiàn)有立法格局和客觀實際,進一步厘清商標(biāo)法上的在先權(quán)利、民法上的姓名權(quán)和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上的商品化權(quán)益的相互關(guān)系。姓名權(quán)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雖均以姓名為客體,但在性質(zhì)上屬于不同的民事權(quán)益,有著不同的保護路徑和條件,現(xiàn)行法律也將其納入不同的保護序列,故應(yīng)將其區(qū)別對待并使其各得其所,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作為一種獨立的民事利益。姓名在商標(biāo)上的使用構(gòu)成功能與目的的轉(zhuǎn)換性使用,即由人格到商業(yè)標(biāo)志的轉(zhuǎn)換,應(yīng)將由此產(chǎn)生的在先法益定性為商業(yè)標(biāo)志性的商品化權(quán)益,而不適宜將其歸入姓名權(quán)。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既要遵循財產(chǎn)權(quán)保護的法律邏輯,又要注重政策考量。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與各國經(jīng)濟、社會、文化和法律傳統(tǒng)息息相關(guān),我國的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不能簡單借鑒國外相關(guān)經(jīng)驗以及僅從概念出發(fā),而是須符合國情、立法狀況和實際需求。
【關(guān)鍵詞】 商標(biāo)法 在先權(quán)利 姓名權(quán) 商品化權(quán)益 喬丹商標(biāo)案
最高人民法院在“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中以姓名權(quán)為名保護了美國公民喬丹的在先權(quán)利。 該案關(guān)于依據(jù)《商標(biāo)法》保護姓名權(quán)的裁判說理,引起較大關(guān)注和強烈反響。隨后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商標(biāo)授權(quán)確權(quán)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法釋〔2017〕2號,以下簡稱《商標(biāo)授權(quán)確權(quán)司法解釋》)第20條規(guī)定,姓名權(quán)可以作為現(xiàn)行《商標(biāo)法》第32條 前段規(guī)定的在先權(quán)利,并明確了相應(yīng)的保護條件,二者是相互呼應(yīng)和可以對照理解的。 “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雖然明確地將姓名權(quán)作為《商標(biāo)法》規(guī)定的在先權(quán)利,但就商標(biāo)授權(quán)確權(quán)中對知名人物姓名的法律保護而言,究竟涉及的是姓名權(quán)還是商品化權(quán)益,究竟如何對其進行定性及采取何種保護態(tài)度,仍是一個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論與實踐問題。鑒于此,本文擬對有關(guān)問題作一些法理上的探討。
一、名不副實的姓名權(quán)保護
“喬丹商標(biāo)案”涉及的核心法條是2001年《商標(biāo)法》第31條,即“申請商標(biāo)注冊不得損害他人現(xiàn)有的在先權(quán)利,也不得以不正當(dāng)手段搶先注冊他人已經(jīng)使用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biāo)”。該案再審判決認(rèn)為姓名權(quán)屬于該條規(guī)定的“在先權(quán)利”,美國公民喬丹享有“喬丹”中文名稱的姓名權(quán),喬丹公司的爭議商標(biāo)損害美國公民喬丹的姓名權(quán)。問題在于,該案再審判決雖基于姓名權(quán)但又是從商業(yè)利益的角度界定姓名權(quán),且援引1993年《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5條第3項支持其對姓名權(quán)的界定。這涉及商標(biāo)法上的在先權(quán)利、民法上的姓名權(quán)與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上的商品化權(quán)益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這是本案的實質(zhì)所在,也是本案并未厘清的核心法律問題。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究竟是姓名權(quán)的組成部分,還是相互獨立和應(yīng)予區(qū)別對待,涉及對我國相關(guān)法律制度的理解、定位和建構(gòu)。從該案再審判決對姓名權(quán)的界定和論述來看,雖然形式上是將商品化權(quán)益納入姓名權(quán),但顯然有姓名權(quán)保護思路與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思路的交織,這既涉及其對姓名權(quán)保護的定位是否準(zhǔn)確,也涉及如何妥當(dāng)對待商品化權(quán)益問題。
(一)姓名權(quán)的保護思路
姓名權(quán)是《民法通則》和《民法總則》所明確列舉的人格權(quán),對姓名權(quán)當(dāng)然需要采取人格權(quán)的保護思路。姓名是對自然人的一種稱謂,構(gòu)成自然人人格的組成部分。姓名權(quán)保護遵循如下思路和條件:認(rèn)定侵犯姓名權(quán)的前提是首先證明姓名是主張權(quán)利者的,然后有干擾姓名權(quán)人使用或者擅自使用他人姓名的行為。只要證明姓名是主張權(quán)利者的,且他人有擅自使用行為,即構(gòu)成侵害姓名權(quán)。如果將姓名權(quán)作為2001年《商標(biāo)法》第31條規(guī)定的在先權(quán)利的一種,按照姓名權(quán)保護思路,只要證明主張姓名權(quán)者是姓名權(quán)人(姓名是權(quán)利人的),他人未經(jīng)許可擅自將其姓名申請注冊為商標(biāo),即構(gòu)成侵害姓名權(quán)。至于該姓名的知名度、姓名權(quán)與申請注冊商標(biāo)之間的市場關(guān)系等,均不屬于侵害姓名權(quán)或者保護姓名權(quán)的要件,充其量只是用于證明誰是姓名權(quán)主體以及是否有侵權(quán)故意的因素。
如果以姓名權(quán)的保護思路衡量“喬丹商標(biāo)案”,只需證明和認(rèn)定“喬丹”確系美國球星Michael Jeffrey Jordan的中文名字(再審判決以大量篇幅認(rèn)定“喬丹”一詞與美國公民喬丹之間存在穩(wěn)定的關(guān)系等當(dāng)屬此意),該姓名受姓名權(quán)保護,而爭議商標(biāo)使用的是該姓名,即構(gòu)成對姓名權(quán)的損害。既然此處的姓名權(quán)是人格權(quán)和絕對權(quán),且屬于2001年《商標(biāo)法》第31條前段規(guī)定之中的在先權(quán)利,而不是后段規(guī)定的“已經(jīng)使用并有一定影響的商標(biāo)”,因而無需認(rèn)定具有一定影響等因素,也即姓名權(quán)并不以知名度為保護要件。
(二)“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在姓名權(quán)保護上的額外考量
“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顯然并未簡單地采取姓名權(quán)保護的思路,而是在姓名權(quán)保護之外考量了多種因素。也即“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雖以保護姓名權(quán)為名,但事實上并不是基于姓名權(quán)本身,而是基于諸多市場因素,尤其是在商標(biāo)保護思路與姓名權(quán)保護思路之間存在明顯的交織和混亂。
首先,再審判決對姓名權(quán)保護條件的認(rèn)定超出了姓名權(quán)保護的要求。其對姓名權(quán)保護設(shè)定了如下三項條件,即該特定名稱在我國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為相關(guān)公眾所知悉,相關(guān)公眾使用該特定名稱指代該自然人,以及該特定名稱已經(jīng)與該自然人建立了穩(wěn)定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該三項條件不是保護姓名權(quán)的酌情考量因素,而被作為“依法主張姓名權(quán)保護”的構(gòu)成要件。 再審判決對姓名權(quán)保護要件的界定與前述侵害姓名權(quán)的構(gòu)成要件明顯不同。
其次,商業(yè)價值是再審判決保護姓名權(quán)的重要基點和依據(jù)。如再審判決認(rèn)為:“在適用商標(biāo)法第三十一條的規(guī)定對他人的在先姓名權(quán)予以保護時,不僅涉及對自然人人格尊嚴(yán)的保護,而且涉及對自然人姓名,尤其是知名人物姓名所蘊含的經(jīng)濟利益的保護。”傳統(tǒng)民法意義上的姓名權(quán)屬于人格權(quán),不具有經(jīng)濟利益的內(nèi)容,充其量只是與經(jīng)濟利益有關(guān),再審判決將經(jīng)濟利益直接解讀為姓名權(quán)的內(nèi)容,顯然已超出人格權(quán)的固有含義。
最后,再審判決按照類似商業(yè)標(biāo)志的思路進行保護。再審判決將引起相關(guān)公眾誤認(rèn)作為給予姓名權(quán)保護的核心考量因素,如特別將“爭議商標(biāo)的具體情形是否會使相關(guān)公眾誤認(rèn)為與再審申請人具有關(guān)聯(lián)”作為一項獨立的判決理由,將姓名權(quán)損害定位為市場損害,將其立足點不僅置于“保護自然人的人格尊嚴(yán)及其姓名所蘊含的經(jīng)濟利益”,還置于“防止相關(guān)公眾誤認(rèn),藉以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quán)益”。而就侵害姓名權(quán)而言,未經(jīng)許可的使用行為即構(gòu)成侵權(quán),此處所謂導(dǎo)致誤認(rèn)等因素已屬損害商業(yè)標(biāo)志的范疇。引起市場誤認(rèn)顯然不是姓名權(quán)保護的考量因素,而恰恰是其商品化的表征和產(chǎn)物。
二、姓名權(quán)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之二元分立保護
就姓名的法律保護而言,存在姓名權(quán)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兩種不同的保護路徑。因法律傳統(tǒng)、立法和保護實際以及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各國對此的保護態(tài)度差別很大。 我國實際上已形成上述二元分立保護(“雙軌制”)的基本立法框架,只是需要在法理上進一步發(fā)掘、梳理和澄清認(rèn)識。
(一)三種代表性的保護模式
世界范圍內(nèi)對姓名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大體上有三種保護模式,一是獨特的和獨立的“公開權(quán)”強保護制度,二是擴展人格權(quán)保護的變通保護制度,三是散見于多種法律的弱保護制度。
首先,關(guān)于姓名的“公開權(quán)”保護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采取了“公開權(quán)”(rights of publicity)制度,知名人物姓名等具有人格特征的商品化權(quán)益被稱為公開權(quán),即控制為商業(yè)目的使用姓名等人格特征的權(quán)利。 美國的公開權(quán)制度是為了保護名人的商業(yè)利益,由判例在隱私權(quán)制度的基礎(chǔ)上逐漸創(chuàng)設(shè)。 隱私權(quán)針對的是行為人對他人尊嚴(yán)和精神的傷害,根據(jù)受害人遭受精神痛苦的程度確定損害的賠償范圍和數(shù)額。公開權(quán)保護個人人格的潛在商業(yè)價值,賦予名人對自己姓名、肖像和其他人格特征進行商業(yè)利用的支配權(quán)利。公開權(quán)本質(zhì)上是可以自由轉(zhuǎn)讓的財產(chǎn)權(quán)。 在姓名的使用上,它對普通人和名人的損害是不同的,即給普通人造成的損害是精神痛苦,損害了其人身權(quán)利即尊嚴(yán)感和精神安寧,所以被歸入“讓其獨處的權(quán)利”(隱私權(quán)),而給名人造成的是財產(chǎn)損害,因為名人的高曝光率已使公開其姓名不再發(fā)生精神損害。 將公開權(quán)作為純粹的財產(chǎn)權(quán),從而與人身權(quán)分割開來,這是該制度的革命意義之所在。
當(dāng)今美國的公開權(quán)制度比較發(fā)達,對于知名人物身份特征的商品化保護最為正面、徹底和完整,且對許多國家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這與其獨特的歷史背景、社會人文基礎(chǔ)和思想淵源密切相關(guān)。例如,美國自20世紀(jì)50年代開始正式承認(rèn)和保護公開權(quán),直接的原因是娛樂業(yè)蓬勃發(fā)展,制造和傳播文化的力量不斷商品化和集中化,明星的社會地位普遍上升,從而使得公開權(quán)逐漸演化為財產(chǎn)權(quán)。美國人非常重視個人成就以及從這些成就中獲得經(jīng)濟利益的權(quán)利。 美國的司法實用主義色彩濃厚,在權(quán)利的創(chuàng)設(shè)和性質(zhì)界定上不固守形式主義和傳統(tǒng)教條,不具有像歐洲大陸法國家那樣根深蒂固的法律教義、法律概念和權(quán)利類型傳統(tǒng),因而能夠靈活地創(chuàng)設(shè)和界定公開權(quán),將其定位為人格之外的財產(chǎn)權(quán),便于確定其法律屬性和拓展其保護范圍。
其次,關(guān)于人格權(quán)的擴展保護模式。這是法國、德國等大陸法系國家采取的保護模式。大陸法系國家有根深蒂固的人身權(quán)與財產(chǎn)權(quán)分立的傳統(tǒng)觀念,但在人格具有經(jīng)濟價值的當(dāng)今時代,在傳統(tǒng)權(quán)利分立觀念的基礎(chǔ)上又進行了變通解釋。例如,大陸法理論上一直認(rèn)為,人格不具商業(yè)性,具有非財產(chǎn)性。在現(xiàn)代社會,財產(chǎn)與人格的關(guān)系越來越緊密,人格越來越財產(chǎn)化,甚至出現(xiàn)了人格具有財產(chǎn)性的主張。例如,某些法國學(xué)者基于人格權(quán)的財產(chǎn)性和非財產(chǎn)性之間的不協(xié)調(diào),主張對兩者分別以不同的即“二元”方法進行保護。法國法院對由人格派生的財產(chǎn)價值進行保護。此外,法國等一些民法法系國家的學(xué)者為了在人格的財產(chǎn)性保護上打破人身權(quán)與財產(chǎn)權(quán)的傳統(tǒng)二元分類結(jié)構(gòu),選擇了一個更為靈活的視角,主張“可以把人格權(quán)財產(chǎn)性方面作為寬泛定義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常見的做法就是把姓名和肖像識別為商標(biāo)”。
受羅馬法思想的影響,《德國民法典》嚴(yán)格區(qū)分人格利益損害與財產(chǎn)損害,認(rèn)為對精神損害予以金錢賠償,與國民的主流觀念相背離。后來德國法院創(chuàng)設(shè)了一般人格權(quán),并承認(rèn)侵害人格權(quán)適用損害賠償責(zé)任。在此基礎(chǔ)上,德國法院將商業(yè)化利用他人肖像或者姓名的行為確認(rèn)為侵犯一般人格權(quán)的行為。德國法院逐漸承認(rèn)某些人格權(quán)利具有財產(chǎn)性質(zhì),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可交易性。但德國創(chuàng)設(shè)一般人格權(quán)主要不是為了保護人格權(quán)的財產(chǎn)價值或他人身份的商業(yè)價值,而是為了保護人格尊嚴(yán)和人的自由發(fā)展。 當(dāng)然,德國的相關(guān)判例情形不一。如德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涉及搖滾歌星肖像保護的“Nena案”中,對于人格是否屬于可轉(zhuǎn)讓的財產(chǎn)未置一詞,而是以未經(jīng)許可使用構(gòu)成不當(dāng)?shù)美麨橛捎枰员Wo。有些判決則依據(jù)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予以保護。 不過,“對于人格權(quán)財產(chǎn)化這個問題,德國法院并沒有像法國和美國法院那樣關(guān)注”,“德國法院一貫做法是不愿意保護人格權(quán)的財產(chǎn)方面,至少不愿意以人格權(quán)的理由來保護那些積極開發(fā)自己人格的名人”。
最后,關(guān)于多種法律混合保護模式。英國法沒有承認(rèn)公開權(quán)概念,也沒有一套獨立的保護制度。英國法院通常不承認(rèn)擅自商業(yè)化使用知名人物姓名或者肖像的訴由。 在英國對名人形象少有保護,只是根據(jù)版權(quán)法、商標(biāo)法、普通法上的假冒訴訟等進行零散的保護,甚至有觀點認(rèn)為這些制度不利于保護名人利益,因而其保護程度遠不及美國等國家。有評論認(rèn)為,美國與英國均未能很好地平衡社會公眾與名人的利益保護,即在美國名人的公開權(quán)保護力度越來越大,社會公眾不能獲得回報,而在英國名人不能因其創(chuàng)造而獲得回報,商業(yè)廣告公司則大賺其錢。
綜上,各國法對于知名人物身份特征的保護態(tài)度差異很大,路徑不一。這與各國歷史、文化、法律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需求的不同有關(guān)。民法法系國家一方面對于賦予人身權(quán)財產(chǎn)價值非常謹(jǐn)慎,另一方面在社會發(fā)展需求的壓力之下又不得不逐漸讓步,于是多在傳統(tǒng)人格權(quán)之下進行變通和擴張,使財產(chǎn)權(quán)與人身權(quán)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引發(fā)眾多爭議。美國則沒有這樣的理論和實踐負擔(dān),而是從實用主義出發(fā),對于知名人物身份特征的商品化權(quán)益有效地加以界定,使相關(guān)法律調(diào)整比較順暢。我國對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進行保護顯然受到了域外法的影響,但須充分考慮各國特殊的制度背景,歸根到底應(yīng)根據(jù)自身的立法狀況、國情和實際需要,確定如何進行保護及其保護程度。
(二)我國法上的二元分立保護模式分析
按照《商標(biāo)授權(quán)確權(quán)司法解釋》,姓名權(quán)是《民法通則》明確規(guī)定的一項權(quán)利,在商標(biāo)領(lǐng)域未經(jīng)許可將他人姓名申請注冊為商標(biāo)并進行使用的行為屬于侵害姓名權(quán)的行為。 但是,我國民事基本法和相關(guān)特別法已在事實上區(qū)分了姓名權(quán)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已獨立于姓名權(quán)之外,兩者分別被納入兩類民事權(quán)益,即姓名權(quán)屬于人格權(quán)范疇,而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屬于財產(chǎn)權(quán)范疇,受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等特別法的保護。而且,商品化權(quán)益經(jīng)常被歸入知識產(chǎn)權(quán)(或者類知識產(chǎn)權(quán)), 最慣常的是由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調(diào)整。因此,現(xiàn)行法律事實上已將兩者納入不同的保護路徑,目前僅需恰當(dāng)?shù)丶右越忉尯徒缍ǎ魑鷥烧咧g的關(guān)系。我國需要根據(jù)自己的國情和需求,構(gòu)建理性的和適當(dāng)?shù)男彰唐坊瘷?quán)益保護制度。筆者認(rèn)為,根據(jù)現(xiàn)行相關(guān)法律制度已能夠構(gòu)建更為融洽的二元保護體系。
第一,《民法通則》對姓名的人格權(quán)保護。姓名權(quán)屬于《民法通則》所規(guī)定的人格權(quán)。該法第99條第1款規(guī)定:“公民享有姓名權(quán),有權(quán)決定、使用和依照規(guī)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盜用、假冒。”該法第120條規(guī)定:“公民的姓名權(quán)……受到侵害的,……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民法通則》是從純粹人格意義上的姓名權(quán)保護出發(fā),針對侵害行為作出只限于特定情形的特別規(guī)定。
首先,姓名權(quán)具有人格性而非財產(chǎn)性。姓名權(quán)承載著豐富的人格和文化含義。例如,姓名是由“姓”與“名”構(gòu)成的稱謂,其中,“姓”的選取“體現(xiàn)著血緣傳承、倫理秩序和文化傳統(tǒng),公民選取姓氏涉及公序良俗”,既是權(quán)利,又是約束。 這典型地體現(xiàn)了其人格性。再如,即使是對于“干涉、盜用、假冒”他人姓名的侵權(quán)行為,“賠償損失”也不是以其具有財產(chǎn)價值為前提,而是基于因侵害人身權(quán)所造成的財產(chǎn)損失,或者是基于精神撫慰,即撫慰金或者精神損失費。 《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20條規(guī)定的“侵害他人人身權(quán)益造成財產(chǎn)損失”,是從已產(chǎn)生財產(chǎn)損失的損害后果上對責(zé)任的規(guī)定,仍以侵害人身權(quán)為前提,并非認(rèn)為人身權(quán)具有財產(chǎn)內(nèi)容。在學(xué)理上,姓名權(quán)被認(rèn)為是以姓名以及與姓名相關(guān)聯(lián)的人格利益為客體。關(guān)于姓名權(quán)的法律屬性有“所有權(quán)說”“無形財產(chǎn)權(quán)說”“親屬權(quán)說”“人格權(quán)說”等不同學(xué)說,但最為通行的是“人格權(quán)說”。 《民法通則》《民法總則》均將其納入人格權(quán)范疇。姓名權(quán)的人格屬性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它具有專有性,與自然人的人身不可分離;它具有非財產(chǎn)性,它本身不具有直接的財產(chǎn)內(nèi)容,也無法體現(xiàn)為確定的財產(chǎn)價值,其客體也不像財產(chǎn)權(quán)客體那樣可以轉(zhuǎn)讓和繼承;姓名是自然人特定化的標(biāo)志,是自然人人格的外在表現(xiàn)。 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是一種可以通過許可使用等方式積極行使的財產(chǎn)性權(quán)益,而不只是排除侵害的消極權(quán)益,因而財產(chǎn)價值是其固有的內(nèi)容,而不是侵害之后的救濟,這是其與人格權(quán)的根本性區(qū)別。
其次,姓名權(quán)保護具有絕對性和純粹性。未經(jīng)許可使用他人姓名即構(gòu)成侵權(quán),認(rèn)定侵害姓名權(quán)通常不必考慮其他的利益平衡因素。“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并未循此思路,如強調(diào)了利益平衡,即“在解決本案涉及的在先姓名權(quán)與注冊商標(biāo)權(quán)的權(quán)利沖突時,應(yīng)合理確定在先姓名權(quán)的保護標(biāo)準(zhǔn),平衡在先姓名權(quán)人與商標(biāo)權(quán)人的利益”。其實,2001年《商標(biāo)法》第31條規(guī)定的不是一般的權(quán)利沖突,而是“侵害在先權(quán)利”,其侵權(quán)構(gòu)成視被侵害的權(quán)利而定。除該條后段特別規(guī)定了“一定影響”等要件外,其他在先權(quán)利無需具備這些要件,只需具備與其權(quán)利相對應(yīng)的構(gòu)成要件。就姓名權(quán)而言,未經(jīng)許可擅自使用他人姓名即構(gòu)成侵害姓名權(quán)。姓名是否具有知名度等不是其保護條件。如果設(shè)定如此的條件,就不再是姓名權(quán)意義上的保護,也即侵害的不再是姓名權(quán),而應(yīng)該是其他民事權(quán)益。也正是由于此類姓名權(quán)保護及其保護要件不再為《民法通則》有關(guān)姓名權(quán)的規(guī)定所支撐,“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又援引1993年《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5條第3項及其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作為依據(jù)。殊不知此時的姓名權(quán)保護已超出人格權(quán)保護的范圍而轉(zhuǎn)化成商品化權(quán)益的保護。即便就該案再審判決而言,它也主張“權(quán)利人可以將其姓名許可給他人進行商業(yè)利用”,只不過認(rèn)為“商業(yè)化利用”之類的財產(chǎn)利益從屬于其人身權(quán)屬性。這種利益平衡的保護思路恰恰契合了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需求。
再次,對他人姓名的“冒用”和“盜用”不同于商標(biāo)上的轉(zhuǎn)換性使用。《民法通則》對姓名權(quán)的保護只限于禁止“干涉、盜用、假冒”他人姓名。 問題在于對他人姓名的一般性“盜用”與擅自用作商標(biāo)是否有區(qū)別,或者是否有必要進行區(qū)分。既然姓名是“指代、稱呼、區(qū)分特定的自然人” 之稱謂,“盜用”和“冒用”的本意必然是發(fā)生自然人人格同一性的誤認(rèn)即“人格混同”,即因冒名頂替或者擅自使用,造成實為自然人甲而名為自然人乙的自然人之間的身份混同和誤認(rèn)。換言之,對他人姓名的“冒用”或“盜用”除具有未經(jīng)許可而使用的表征外,其實質(zhì)是被使用的姓名指向自然人個人,也即使用的結(jié)果是造成自然人人格意義上的同一性混淆。 這是“冒用”或者“盜用”的固有含義。商標(biāo)則是商品(包括服務(wù))的指稱和標(biāo)志,將他人姓名用作商標(biāo),就是將姓名的自然人指稱和識別意義變成了商品的指稱和識別意義,其雖在形式上仍可歸結(jié)為未經(jīng)許可使用他人姓名,但其實質(zhì)意義已發(fā)生根本變化。此即發(fā)生指示對象的屬性轉(zhuǎn)換,在使用的功能和目的上發(fā)生實質(zhì)變化。這種轉(zhuǎn)換性使用已超出避免自然人“人格混同”本來意義上的人格權(quán)保護范圍,不再是導(dǎo)致自然人之間的人格同一性“混淆”,而只是在姓名與被標(biāo)示的商品之間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即使人誤認(rèn)為后者系該自然人生產(chǎn)或經(jīng)營的商品,或者兩者有許可使用姓名的關(guān)系,因而可以與侵害姓名權(quán)的“盜用”和“假冒”明顯區(qū)別開來。這種轉(zhuǎn)換性使用導(dǎo)致的使用行為性質(zhì)的實質(zhì)性改變,恰恰為切斷其與人格權(quán)的聯(lián)系而被歸入商品化權(quán)益意義上的財產(chǎn)權(quán)提供了法理基礎(chǔ),也因此能夠在商業(yè)標(biāo)識保護法或者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上將其定性為市場混淆關(guān)系。例如,世界知識產(chǎn)權(quán)組織“反不正當(dāng)競爭示范條款” 第2條將使用知名人物的姓名作為造成市場混淆的情形之一,原因是將其在商品上使用會與知名人物的商譽或者名聲發(fā)生混淆或者有混淆之虞。 鑒于此,基于權(quán)利內(nèi)容的同質(zhì)性要求,為維持姓名權(quán)的人格權(quán)屬性,可以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從姓名權(quán)中剝離出去。
最后,恰當(dāng)定位姓名的財產(chǎn)價值。姓名權(quán)本不包括商品化權(quán)益,只是因知名人物“名氣”的商業(yè)價值遂具有商標(biāo)價值和可保護的財產(chǎn)法益,但因各國國情的差異,對其的保護方式和保護態(tài)度又不盡相同。無論是變通傳統(tǒng)保護制度而在“舊瓶”中裝入“新酒”,還是考量保護的徹底性、妥當(dāng)性和必要性而另起爐灶,都需要視本國國情而定。在我國通過擴展人格權(quán)的方式保護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并非絕對行不通,但在沒有歷史傳統(tǒng)束縛和能夠予以獨立保護的背景下,對于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給予人格權(quán)之外的獨立保護,是一種更為徹底、更為充分和更符合問題本質(zhì)的保護路徑選擇,同時又能夠維護姓名權(quán)的內(nèi)在同質(zhì)性,實現(xiàn)邏輯上的自洽。而且,承認(rèn)姓名商品化權(quán)益的獨立性,可以使其成為一種能夠通過許可使用等方式積極行使的財產(chǎn)性權(quán)益,從而與更側(cè)重于消極排除侵害的姓名權(quán)相區(qū)別。 況且我國已事實上形成了姓名權(quán)與姓名商品化權(quán)益分立保護的立法格局,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等特別法對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另有保護。“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正因未劃清姓名權(quán)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之間的界限,導(dǎo)致其在法律之間的關(guān)系、保護要件、考量因素等問題上的思路頗為混亂。
第二,《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對姓名的商業(yè)化保護。“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認(rèn)為,1993年《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5條第3項針對的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本質(zhì)上是損害他人姓名權(quán)的侵權(quán)行為,該行為“所涉及的‘引人誤認(rèn)為是他人商品’,與本案中認(rèn)定爭議商標(biāo)的注冊是否容易導(dǎo)致相關(guān)公眾誤認(rèn)為存在代言、許可等特定聯(lián)系”密切相關(guān),可參照適用其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確定自然人姓名權(quán)保護的條件。這種對1993年《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5條第3項規(guī)定的解讀并不符合法律的本意。相反,該第5條第3項規(guī)定的“姓名”并非立足于姓名權(quán),將其解讀為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更為妥當(dāng)。換言之,該法雖然規(guī)定的是使用“姓名”,實質(zhì)損害的是具有商業(yè)標(biāo)志屬性的財產(chǎn)權(quán)益。
根據(jù)1993年《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起草者的解釋,“擅自使用他人的企業(yè)名稱或者姓名引起的后果是引人誤解為被冒用者的商品或者服務(wù),這樣就會損害被冒用者的商品銷售或者提供服務(wù),形成了不正當(dāng)競爭。”一些國家一般要求此種情形下的姓名等必須“國內(nèi)周知”或者“以相關(guān)大眾所共知”,我國法的上述規(guī)定雖未如此要求,但 “含義和他們是一樣的”。 顯然,這是基于商業(yè)標(biāo)識意義的考量而制止對姓名的仿冒性使用,而姓名權(quán)保護是不需要考慮知名度、市場誤導(dǎo)等要素的。2017年修訂后的《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6條更是將其修訂為純粹的遏制“混淆行為”的商業(yè)標(biāo)識保護條文,其第2項規(guī)定了“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響的企業(yè)名稱(包括簡稱、字號等)、社會組織名稱(包括簡稱等)、姓名(包括筆名、藝名、譯名等)”的行為,將“有一定影響”“引人誤認(rèn)為是他人商品或者與他人存在特定聯(lián)系”等市場要素明確規(guī)定為構(gòu)成要件,其商業(yè)標(biāo)識保護意圖更為明確和凸顯。
《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不正當(dāng)競爭民事案件應(yīng)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第2款規(guī)定:“在商品經(jīng)營中使用的自然人的姓名,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五條第(三)項規(guī)定的‘姓名’。具有一定的市場知名度、為相關(guān)公眾所知悉的自然人的筆名、藝名等,可以認(rèn)定為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五條第(三)項規(guī)定的‘姓名’。”如該司法解釋起草者所言:“《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對于企業(yè)名稱和姓名的保護立足于制止仿冒行為。《民法通則》對于企業(yè)名稱和自然人姓名的保護作出了基本的規(guī)定,這些規(guī)定除具有確認(rèn)基本民事權(quán)利的意義外,主要是立足于保護人身權(quán)的角度保護企業(yè)名稱和姓名的。《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保護企業(yè)名稱和姓名的目的則是制止造成市場混淆的不正當(dāng)競爭行為。”“自然人的姓名與特定的商品聯(lián)系起來時,也可以產(chǎn)生識別商品來源的作用。”“姓名在具有商品來源的標(biāo)識意義時,受《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5條第3項規(guī)定的保護。” 而且,1993年《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5條第3項雖然沒有要求所保護的“姓名”知名或者有一定影響,但其中“引人誤認(rèn)為是他人商品”的規(guī)定已包含了市場知名度因素。顯然,該司法解釋對于姓名的商業(yè)標(biāo)識定位符合《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立法本意,而且也是據(jù)此設(shè)定保護條件的。這些保護實踐也為2017年修訂后的《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6條第2項所吸收。該法對于姓名的保護顯然不再是《民法通則》第120條所規(guī)定的姓名權(quán)意義上的保護,而是意在制止仿冒行為的商業(yè)標(biāo)識保護。
相關(guān)司法實踐早已采取將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上的姓名作為商業(yè)標(biāo)識保護的態(tài)度。如在姚明與武漢云鶴公司不正當(dāng)競爭案中,武漢云鶴公司擅自將姚明的姓名、肖像及包含姚明姓名的“姚明一代”作為商業(yè)標(biāo)識使用在其生產(chǎn)、經(jīng)銷的運動鞋、服裝等體育用品上,還在網(wǎng)站及商業(yè)廣告中使用姚明的姓名、肖像和簽名進行宣傳。二審判決認(rèn)為:“受《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保護的自然人姓名,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人身權(quán),是區(qū)別不同市場主體的商業(yè)標(biāo)識。未經(jīng)權(quán)利人授權(quán)或許可,任何企業(yè)或個人不得擅自將他人姓名、肖像、簽名及其相關(guān)標(biāo)識進行商業(yè)性使用。” 此種保護定位的直接意義是可以完全按照財產(chǎn)損失的方式確定損害賠償額,合乎法律規(guī)定的本意。
從商業(yè)標(biāo)識和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角度保護姓名等商品化權(quán)益是國際上一種比較主流的認(rèn)識。如世界知識產(chǎn)權(quán)組織“反不正當(dāng)競爭示范條款”第2條列舉的引起市場混淆的典型標(biāo)志,包括商標(biāo)和商號外的商業(yè)標(biāo)識、商品外觀、商品或者服務(wù)的介紹以及“知名人物或者知名的虛擬角色”。美國等國家將對姓名等身份特征的商業(yè)化保護納入商業(yè)標(biāo)識和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的保護范圍。例如,“隨著各種身份特征被越來越多地加以商業(yè)化使用,特別是在新科技市場的潛在需求下,當(dāng)今社會越來越強調(diào)商標(biāo)、名譽以及姓名的識別價值,因此人格(至少是名人的人格)變得越來越財產(chǎn)化。” 美國法院在“Athans案”和“White案”中認(rèn)為,曾開發(fā)過自己肖像商業(yè)價值的名人對其肖像享有一項類似于商標(biāo)權(quán)的權(quán)利。 “在涉及名人代言混淆的案件里,所謂‘商標(biāo)’是指名人的人格身份。”“所謂‘原告商標(biāo)的強度’則是指名人在社會成員中被識別出來的程度。” 在美國,知名人物“公開權(quán)”的保護問題被納入《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重述(第三版)》。 美國大多數(shù)法院通常將公開權(quán)視為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領(lǐng)域的問題。 我國1993年《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5條第3項和2017年修訂后的《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6條第3項對于姓名的保護態(tài)度與國際趨勢相吻合,而且前述立法史和司法實踐足以印證其屬于商品化權(quán)益意義上的保護。
第三,遵循各行其道的保護格局。如前所述,“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明確將其保護對象定位為“姓名權(quán)”和“人身權(quán)”,但實質(zhì)的立足點是商品化權(quán)益,強調(diào)人身權(quán)中的經(jīng)濟利益,并在此基礎(chǔ)上為將“姓名權(quán)”納入2001年《商標(biāo)法》第31條規(guī)定的“在先權(quán)利”設(shè)定了三項條件,使此處保護的姓名權(quán)又不同于民法上的姓名權(quán)。這種紊亂的認(rèn)識必然導(dǎo)致名實不符的后果,即雖然以保護姓名權(quán)為名,但實際保護的是“自然人姓名,尤其是知名人物姓名所蘊含的經(jīng)濟利益”,以及防止“導(dǎo)致相關(guān)公眾誤認(rèn)為標(biāo)記有該商標(biāo)的商品或者服務(wù)與該自然人存在代言、許可等特定聯(lián)系”,從而損害消費者權(quán)益。 《商標(biāo)授權(quán)確權(quán)司法解釋》第20條規(guī)定:“當(dāng)事人主張訴爭商標(biāo)損害其姓名權(quán),如果相關(guān)公眾認(rèn)為該商標(biāo)標(biāo)志指代了該自然人,容易認(rèn)為標(biāo)記有該商標(biāo)的商品系經(jīng)過該自然人許可或者與該自然人存在特定聯(lián)系的,人民法院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該商標(biāo)損害了該自然人的姓名權(quán)。” 此處也是基于相關(guān)公眾的市場混淆認(rèn)定損害姓名權(quán),其判斷依據(jù)已超出人格權(quán)范圍,其表達方式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接近于1993年《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5條第3項,顯然不再是民法意義上的侵害姓名權(quán)。2017年修訂后的《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6條第2項的規(guī)定更是如此。在我國法律對此已另有保護定位和路徑的情況下,仍將此種情形歸入侵害姓名權(quán)的范圍,并不符合姓名權(quán)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分立保護的立法格局。而且,與1993年《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5條第3項類似,該司法解釋雖未明確要求受此種保護的姓名具有知名度,但能夠達到誤導(dǎo)公眾效果的姓名必然是有知名度的,而且該保護必然是基于知名人物姓名的商業(yè)價值。“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即是該司法解釋規(guī)定的直接注解。鑒于此,知名人物的姓名可以納入商業(yè)標(biāo)識保護的范疇,如此定位就可以將知名度、誤導(dǎo)混淆確定為保護條件,從而順理成章地將其納入現(xiàn)行《商標(biāo)法》第32條后段所規(guī)定的“有一定影響的商標(biāo)”。“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設(shè)定的“一定影響”“誤導(dǎo)混淆”等保護條件恰與此種保護定位相吻合。
我國事實上已形成由民法在人格權(quán)意義上保護姓名權(quán),而由特別法保護姓名(包括筆名、藝名、譯名等)的商品化權(quán)益的二元保護立法格局。應(yīng)當(dāng)將特殊情況下的姓名使用或者知名人物姓名的商業(yè)化利用納入相應(yīng)的特別法進行特別調(diào)整。例如,筆名等在著作權(quán)法中受署名權(quán)保護,而對姓名的商業(yè)化利用受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商標(biāo)法的相應(yīng)保護。這種在人格權(quán)保護之外的特別保護,既可以避免將與人格異質(zhì)的財產(chǎn)權(quán)益納入人格權(quán)一般保護的范圍,又可使應(yīng)該保護的財產(chǎn)利益得到正面的和積極的保護,因而更適合這些特殊權(quán)益的保護需求,也更契合我國目前的法律保護序列、格局和態(tài)度。以姓名權(quán)為名保護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則是貌合神離的。“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是在承認(rèn)喬丹姓名的商品來源識別意義的基礎(chǔ)上予以保護,而不是給予一般性的姓名權(quán)保護。而且,在姓名權(quán)之外對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進行單獨的保護,可以使其保護邊界具有彈性和相對性,不再像姓名權(quán)保護那樣具有絕對性,便于進行利益平衡、適當(dāng)限制其保護范圍以及妥善處理其與商業(yè)標(biāo)識保護的關(guān)系。因此,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作為商標(biāo)法上的在先權(quán)利,更適宜從商業(yè)標(biāo)志意義上進行理解和界定。
三、姓名權(quán)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二元分立保護的必要性與正當(dāng)性
在我國涉及知名人物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的既有民事裁判,也有行政裁判。 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之所以應(yīng)作為一種不同于姓名權(quán)和人格權(quán)的獨立財產(chǎn)權(quán)益,其正當(dāng)性和必要性源于兩種保護的根本差異,以及如何處置更能夠?qū)崿F(xiàn)制度配置的優(yōu)化。
(一)保護路徑的選擇取決于權(quán)利性質(zhì)的差異
首先,存在平等保護與區(qū)別保護上的差異。姓名權(quán)屬于人身權(quán)中的人格權(quán),對其的保護應(yīng)該是純粹的、一視同仁的和人人平等的,不應(yīng)該因自然人的知名度不同而有差異。商品化權(quán)益則是以姓名的知名度為保護要件,是少數(shù)知名人物的“特權(quán)”。如果仍將其視為人格權(quán)予以保護則難以自圓其說,也會破壞人格權(quán)保護的基本價值。尤其是如果將姓名權(quán)納入商標(biāo)法中的在先權(quán)利,且將知名度作為保護條件,必然導(dǎo)致人格權(quán)保護上的歧視,這種立論的正當(dāng)性不足。但是如果將非知名人物的姓名作為商標(biāo)法中的在先權(quán)利進行保護,又完全沒有必要。 如果將其定性為財產(chǎn)權(quán),其保護的正當(dāng)性就不再成為問題。因為此時財產(chǎn)權(quán)保護的前提是姓名具有商業(yè)價值,但并非所有人的姓名都具有商業(yè)價值,知名度也就可以成為具有正當(dāng)性的保護條件。因此,將其納入財產(chǎn)權(quán)予以保護并設(shè)定知名度等條件就解決了保護的正當(dāng)性問題,也不破壞人格權(quán)保護的固有和諧性。
這種正當(dāng)性難題并非虛構(gòu)。美國法因為其人格與財產(chǎn)絕對分立的傳統(tǒng)以及直接將其定位為財產(chǎn)權(quán),就不存在這方面的正當(dāng)性難題。但大陸法國家卻有如此難題。例如,公開權(quán)(商品化權(quán))將名人與普通人區(qū)別對待的正當(dāng)性是保護此類權(quán)益的“諸多難題中尤為突出的”問題。大陸法學(xué)者對此進行了頗費周折的解釋。例如,“一些學(xué)者把這種區(qū)別對待看作是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形式的特權(quán)’”;“雖然這個問題可以簡單看作是一個經(jīng)濟問題,即名人通過強調(diào)他們的金錢損失可以得到更多的補償,而同時普通人通過強調(diào)精神損害也會得到一些更好的結(jié)果。但是,確切地說,在對待人格權(quán)保護及其市場開發(fā)這個問題上,的確是存在歧視的,不過當(dāng)我們用財產(chǎn)觀點解釋這個問題時,就會掩蓋這種區(qū)別。” 我國《民法通則》和《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分別確立了姓名保護的不同定位,此時以務(wù)實的態(tài)度將人格的商品化權(quán)益獨立出來,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礙,反而更易于證成其正當(dāng)性依據(jù)。
其次,能夠?qū)崿F(xiàn)法律保護的內(nèi)在融貫。將商品化權(quán)益定位為獨立法益,有利于解決保護中的悖論,實現(xiàn)權(quán)益內(nèi)部關(guān)系的融通。一是它能夠確保權(quán)利本身的純粹性和避免異質(zhì)性。將商品化權(quán)益歸入姓名權(quán),必然使人格權(quán)增加人格之外的財產(chǎn)內(nèi)容,使姓名權(quán)不倫不類和不合邏輯。二是它能夠使商品化權(quán)益更符合其本身的性質(zhì)。商品化權(quán)益雖然以姓名等人格特征為客體,但不是由人格自然派生的,而是因知名度具有商業(yè)價值而產(chǎn)生,因而具有獨立的屬性、內(nèi)涵和成立要件。它具有完整的權(quán)利內(nèi)容,既包括積極行使的權(quán)能,又包括排斥他人侵害的權(quán)能。相反,將其歸入人格權(quán),必然因性質(zhì)上的錯位發(fā)生邏輯上的混亂。如“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囿于其人格權(quán)認(rèn)識,認(rèn)為“姓名權(quán)本身既不能與權(quán)利人的人身完全分離,也不能完全轉(zhuǎn)讓”。但事實上商品化權(quán)益可以完全轉(zhuǎn)讓。
最后,更適合商標(biāo)法保護在先權(quán)利的場景。獨立的商品化權(quán)益更能夠契合商標(biāo)法上的在先權(quán)利保護。一是現(xiàn)行《商標(biāo)法》第32條規(guī)定的“在先權(quán)利”雖然具有兜底性,但能夠納入其中的“在先權(quán)利”必定與商標(biāo)具有連接點,也即適合于《商標(biāo)法》第31條語境下的“在先權(quán)利”保護。知名人物的姓名具有市場價值,也即有申請注冊商標(biāo)可以利用的市場價值,此時將其納入“在先權(quán)利”才具有實質(zhì)意義。無論是否有主觀上的覺知,很難說“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實質(zhì)上不是將其作為商業(yè)標(biāo)識進行保護的,這也是該判決以利益平衡的態(tài)度對待此類姓名保護的緣由。二是便于妥當(dāng)?shù)亟鉀Q相關(guān)權(quán)利沖突。例如,對于因超過法定期限而已成為不可爭議的注冊商標(biāo),不宜再以侵害姓名權(quán)為由主張民事救濟。這是因為即便不可爭議商標(biāo)使用的是知名人物的姓名,但這畢竟是一種轉(zhuǎn)換性的和商業(yè)標(biāo)志性的使用,法定期間的經(jīng)過意味著該使用已使該姓名與注冊商標(biāo)核定使用的商品之間建立了事實上和法律上的固化關(guān)系,在法律意義上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權(quán)益不能再進入不可爭議商標(biāo)的使用領(lǐng)域。這與人格權(quán)的排斥力有所不同。
(二)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具有獨立構(gòu)成要素
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有其獨立的保護客體、要件和內(nèi)容。首先,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仍以姓名為客體。姓名可以是姓名權(quán)的客體,也可以是商品化權(quán)益的客體。兩者的聯(lián)系是均以姓名為客體,但性質(zhì)不同,即前者為人格權(quán),后者為財產(chǎn)權(quán)。前者人人可以享有,是普適的重要人格利益的權(quán)利化;后者只限于知名人物享有,不具有普適性。商品化權(quán)益能夠獨立存在的重要基礎(chǔ)乃是姓名與姓名權(quán)具有可分性。姓名權(quán)是以姓名為客體的人格權(quán),但姓名并非只能產(chǎn)生姓名權(quán),也即姓名并非只能作為姓名權(quán)的客體。姓名權(quán)是人格權(quán),不具有財產(chǎn)內(nèi)容,這是其作為人格權(quán)的應(yīng)有之義。因姓名的知名度而產(chǎn)生的商業(yè)價值和財產(chǎn)利益,賦予姓名新的權(quán)益內(nèi)涵,承載了財產(chǎn)法益,其本身當(dāng)然可以是一種財產(chǎn)權(quán),沒必要將其當(dāng)然地歸入姓名權(quán)之列。對其更為準(zhǔn)確的界定是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它充其量屬于民事利益的范疇。
其次,商品化權(quán)益有獨立的保護要件。區(qū)分姓名權(quán)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可以更好地設(shè)定各自的保護條件。姓名權(quán)雖然不具有絕對的排他性,但在保護上是一視同仁的,不因知名度高低等而區(qū)分不同的保護條件。而且,《民法通則》對于姓名權(quán)的保護是基礎(chǔ)性保護,即限于禁止干涉、盜用和假冒層面上的保護,這使得同等保護具有可行性,也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人人可得而享的人格權(quán)。基于這種保護定位顯然不適合將其納入2001年《商標(biāo)法》第31條所規(guī)定的在先權(quán)利之范圍,因為此處的在先權(quán)利出現(xiàn)于《商標(biāo)法》,通常需要考慮市場要素,這也是“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自然而然尋求商業(yè)性保護條件的原因。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之享有取決于知名度等市場要素,具有比姓名權(quán)更多的保護要素和更高的保護門檻。而且,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具有不確定性,還需要更多地與公共政策相協(xié)調(diào)。“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已具保護姓名的商業(yè)化價值之實,只是未正其名,結(jié)果導(dǎo)致名與實之間的悖論和乖離。例如,該判決同時援引1993年《反不正當(dāng)競爭法》第5條第3項為姓名權(quán)的保護設(shè)定條件,這說明僅以民法上的姓名權(quán)條款還不能為保護喬丹姓名的商業(yè)利益提供充分的依據(jù)。實際上,這顯然不屬于法律依據(jù)是否充分的問題,而屬于如何認(rèn)識其法律屬性的問題。
姓名受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的基本條件是姓名具有知名度和商業(yè)價值,而知名度又是商業(yè)價值的前提。受保護的姓名必須具有知名度,且知名度必須達到具有商業(yè)價值或者能夠帶來商業(yè)利益的程度。商業(yè)價值也是衡量是否達到必要知名度的標(biāo)尺。例如,在“Carson v. Here’s Johnny Portable Toilets, Inc.案”中,被告是一家生產(chǎn)坐便器的公司。被告為了銷售其產(chǎn)品,使用了“Here’s Johnny”作為商標(biāo)。原告起訴被告侵犯了自己的公開權(quán),請求判令被告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判決認(rèn)為,盡管被告沒有使用Carson的姓名和肖像,但使用原告的綽號“Here’s Johnny”清楚地指明了原告的身份,故被告未經(jīng)授權(quán)就擅自為了商業(yè)利益使用原告的身份,侵犯了原告的公開權(quán)。判決還特別強調(diào),如果被告使用原告的姓名,則不構(gòu)成對原告公開權(quán)的侵犯。因為原告的姓名沒有使其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人;相反,原告的綽號使其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故使用原告的姓名并未侵犯原告的公開權(quán)。 這種知名度的要求顯然與姓名權(quán)保護不同。
最后,商品化權(quán)益有其獨特的保護內(nèi)容。例如,公開權(quán)保護的商業(yè)價值是“認(rèn)可、有吸引力的風(fēng)格以及良好的名聲等”,“它們都有利于提升商品的競爭力或者有助于貨物的銷售”。這些價值(類似于商譽)是“財產(chǎn)性人格權(quán)的核心,而且這些品質(zhì)也使得名人的權(quán)利不同于普通人的權(quán)利”。 它保護“原告在排他地市場化開發(fā)利用其人格、形象和姓名方面的所有權(quán)利”。 “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認(rèn)為,該案姓名權(quán)保護“不僅涉及對自然人人格尊嚴(yán)的保護,而且涉及對自然人姓名,尤其是知名人物姓名所蘊含的經(jīng)濟利益的保護”,特別是“代言、許可等特定聯(lián)系”的商業(yè)價值。可見,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所保護的是其知名度所蘊含的市場價值或者品牌價值。
(三)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定位為受法律保護的民事利益
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獨立于姓名權(quán),屬于一種財產(chǎn)性權(quán)益,而非人格權(quán)。當(dāng)然,人格的商品化權(quán)益與人格仍然關(guān)系密切,在性質(zhì)上屬于以姓名、肖像等特定人格特征為客體的財產(chǎn)性權(quán)益。之所以將其定位為財產(chǎn)性權(quán)益,還是因為法律不能隨意創(chuàng)設(shè)權(quán)利。“除非有清晰的、有說服力的證據(jù)表明存在著某種重要的社會利益,該利益要求法律創(chuàng)設(shè)一項財產(chǎn)權(quán)為之服務(wù),否則,法律不能隨便地創(chuàng)設(shè)財產(chǎn)權(quán)利。”“在娛樂業(yè)的領(lǐng)域里,似乎還不存在充分的社會利益要求法律創(chuàng)設(shè)出一項新的財產(chǎn)權(quán)利。” 就我國的具體情況而言,無論是其權(quán)益本身的確定性還是創(chuàng)設(shè)權(quán)利的必要性,知名人物人格特征的商品化尚不符合權(quán)利化的條件,僅適宜作為民事利益而存在。
我國民法保護的民事權(quán)益包括民事權(quán)利和利益。《民法總則》第126條更是明確規(guī)定:“民事主體享有法律規(guī)定的其他民事權(quán)利和利益。”權(quán)利與利益的基本區(qū)別在于,權(quán)利是法律對利益的類型化規(guī)定,其內(nèi)容和范圍是確定的;利益則是權(quán)利之外的法益。商品化權(quán)益屬于可受法律保護的民事利益,尚難以構(gòu)成一項獨立的權(quán)利,而且保護條件和范圍等尚不確定,需要視具體情況而定。美國公民喬丹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屬于財產(chǎn)法益的范疇,超出了姓名權(quán)范圍,是一種商業(yè)標(biāo)志意義上的法益。將其定位為財產(chǎn)性民事利益,可以使其保護范圍和條件具有靈活性和彈性,既符合人格特征的商品化屬性,又可以靈活把握保護客體和范圍,有助于理順其與相關(guān)權(quán)利的一系列保護關(guān)系。
四、形式主義與功能主義: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中的法律因素與政策因素
保護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既涉及法律因素,又涉及政策因素,需要妥善處理法律與政策的關(guān)系。
(一)形式主義與功能主義
就方法論而言,保護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涉及形式主義和功能主義兩種進路。形式主義是一種邏輯方法和法律思路,它首先是對特定權(quán)益進行法律定性,然后可根據(jù)由此確定的權(quán)益“標(biāo)簽”,對號入座式地界定其相應(yīng)的法律屬性和內(nèi)容。 例如,如果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確定為財產(chǎn)性權(quán)益,則財產(chǎn)的可轉(zhuǎn)讓性、可繼承性及其他屬性隨之適用于該權(quán)益。功能主義則是一種政策方法,即根據(jù)政策效果決定是否應(yīng)當(dāng)將特定權(quán)益確定為財產(chǎn)性權(quán)益,并相應(yīng)地確定其保護范圍大小和程度高低。通常而言,就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而言,在決定是否保護及如何保護的制度形成過程中,功能主義居主導(dǎo)地位;在受保護權(quán)益的定位明晰之后,形式主義居主導(dǎo)地位。美國法上的公開權(quán)制度典型地經(jīng)歷了這種過程。 我國目前對商品化權(quán)益的保護尚不成熟,此時需要兼顧功能主義與形式主義。兩者相結(jié)合,主要是以形式主義為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定性,以功能主義適當(dāng)確定和調(diào)適其保護范圍和程度。
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首先是一種財產(chǎn)性權(quán)益,需要賦予財產(chǎn)權(quán)的基本特性,按照財產(chǎn)類權(quán)益進行塑造和保護。但它畢竟是一種民事利益,具體確定其保護客體、范圍、程度及與其他權(quán)利之間的關(guān)系,則需要考慮政策效果。我國目前尚處于確立和保護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的初期,更需對其保護范圍和程度謹(jǐn)慎確定,對于作為權(quán)益客體的人格特征及其保護條件,應(yīng)當(dāng)在進行充分的利益衡量之后謹(jǐn)慎確定。因此,應(yīng)首先將商品化權(quán)益明確地定位為財產(chǎn)法益,據(jù)此不再扭曲法律的適用。這是形式主義和法律確定性的需要。其次,不急于徑行將商品化權(quán)益歸入權(quán)利,以利益保護的方式保持適當(dāng)?shù)撵`活性和不確定性,以便應(yīng)對復(fù)雜的人格特征商業(yè)化情形,為將來的發(fā)展留有余地。亦如美國學(xué)者所言:“我們要做的應(yīng)當(dāng)是分析公開權(quán)的特性和范圍,并通過政策考量從而判定是應(yīng)當(dāng)擴張還是應(yīng)當(dāng)限縮公開權(quán)的范圍。” “法官和學(xué)者不應(yīng)沉迷于‘財產(chǎn)三段論’的推理方法,……在個案中對所涉及的各項政策進行權(quán)衡分析,通過政策考量進而確定法律是否應(yīng)當(dāng)對某項權(quán)利進行保護。” 我國相關(guān)司法解釋和裁判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定位為姓名權(quán),客觀上會導(dǎo)致姓名權(quán)名實之間的錯位,也會導(dǎo)致在界定權(quán)利邊界時的一些困境。將其納入民事利益意義上的財產(chǎn)法益,就可以靈活處置一些法律適用問題,實現(xiàn)法律因素與政策因素的恰當(dāng)結(jié)合。
在商標(biāo)授權(quán)確權(quán)案件中,對于姓名權(quán)能否作為在先權(quán)利保護,曾有不同的認(rèn)識和做法。這種狀況無疑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的定位有關(guān)。如果采取形式主義方法,將其定位為獨立于人格權(quán)之外的財產(chǎn)利益,且以具有相應(yīng)的知名度為保護要件,可名正言順地以財產(chǎn)權(quán)的方式進行保護并解決自然人死亡之后的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問題。如對于使用已故知名人物姓名的情形,因年代已久且已不存在法定序位的繼承人,此時能否歸入“不良影響”等絕對禁用事由予以保護,純屬政策考慮問題。倘若對社會公眾有商業(yè)價值之外的重大誤導(dǎo),如有違社會主流價值觀,造成政治和社會的不良影響,可以考慮通過商標(biāo)的絕對禁用事由予以制止。
根據(jù)《商標(biāo)授權(quán)確權(quán)司法解釋》第5條第2款的規(guī)定,“將政治、經(jīng)濟、文化、宗教、民族等領(lǐng)域公眾人物姓名等申請注冊為商標(biāo)”,屬于現(xiàn)行《商標(biāo)法》第10條第1款第8項規(guī)定的“其他不良影響”情形。一方面,將這些公眾人物的姓名等人格特征列入商標(biāo)的禁用事由,應(yīng)當(dāng)是考慮到其超出了私人利益的范圍而涉及公共利益,因此其范圍不宜太寬,既要對知名度有較高要求,又要限定為屬于造成市場價值損害以外的重大不良影響。我國公權(quán)力機構(gòu)一向有主動干預(yù)的“偏好”和“家長情結(jié)”,擴張此類公眾人物的范圍會為公權(quán)力機構(gòu)的主動干預(yù)提供依據(jù),也不利于調(diào)動權(quán)利人行使私權(quán)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受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的知名人物通常都是有可能將其人格特征商業(yè)化利用的娛樂、體育等行業(yè)的公眾人物,而不是政治等領(lǐng)域的公眾人物。政治等領(lǐng)域的公眾人物的姓名不能用于市場利用,不具有市場價值。而且,出于政治影響和社會形象等公共利益考量,需要將其納入商標(biāo)的絕對禁用事由。相反,屬于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范圍的公眾人物,對其姓名的使用不宜再列入“不良影響”的絕對禁用事由之列,而只應(yīng)將其納入私權(quán)保護范圍。這也說明需要對能夠受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的公眾人物設(shè)定保護范圍和條件。例如,美國公民喬丹在中國算得上體育領(lǐng)域的公眾人物,如果認(rèn)為其屬于《商標(biāo)授權(quán)確權(quán)司法解釋》第5條第2款規(guī)定的公眾人物范圍,那么意味著對喬丹公司已超過法定撤銷(無效)期間的其他注冊商標(biāo)仍可以“不良影響”為由禁注和認(rèn)定無效。這種解釋顯然行不通,事實上美國公民喬丹在其他系列案件中的相應(yīng)主張也未獲法院支持。
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從來都是以適度為原則, 也不輕易禁止“搭便車”, 這是由需要平衡多種利益所決定的。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同樣如此,尤其是知名人物的知名度由多種原因促成,對其保護應(yīng)適可而止。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最終取決于如何符合國家的發(fā)展需要和適應(yīng)現(xiàn)實需求,其間有大量的政策空間,因此,其保護范圍和程度只能有相對的公平,沒有絕對的道德正當(dāng)性和公平問題。
(二)兩種因素與外國人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
無論是外國人的本名還是中文譯名,其在中國受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需要符合一定的條件。首先,外國人姓名與主張權(quán)利者具有指向關(guān)系上的“可識別性”,即所涉姓名的文字并不要求與主張權(quán)利者具有唯一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它還可能被其他人用作姓名,但就所涉爭議而言,該姓名必須能夠被認(rèn)定為指向主張權(quán)利者,兩者需具有對應(yīng)關(guān)系。無論是外國人的本名、中文名還是本名或者中文名的一部分,只要與姓名權(quán)人有明確的指向關(guān)系,即符合保護條件。其次,外國人姓名必須在中國有實際使用,并具有知名度。正是由于在中國實際使用了姓名,具有一定影響的該姓名才可能在中國市場上具有市場價值。該使用應(yīng)當(dāng)是指主動使用或者對他人使用的認(rèn)可,單純的“被使用”通常不符合獲取權(quán)利的條件。至于是否要求有實際的商業(yè)化使用,完全屬于保護標(biāo)準(zhǔn)的具體考量問題,不存在保護水準(zhǔn)夠不夠的問題,保護國具有酌情確定的自由,可以兼用法律與政策的方法。通常而言,潛在的市場價值也屬于保護之列,未作實際的商業(yè)化使用不影響保護其商品化權(quán)益。
“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認(rèn)為,姓名的使用是姓名權(quán)人的權(quán)利而非義務(wù),不是受保護的前提條件,可以“就其并未主動使用的特定名稱獲得姓名權(quán)的保護”。如果不要求在中國境內(nèi)的實際使用,即與我國法律保護沒有連接點,而且可能使其在國外的“公開權(quán)”自然延伸到我國,這與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的地域性不符。再審判決還認(rèn)為,根據(jù)商標(biāo)法主張姓名權(quán),其保護并不以主動使用為條件。但是,至少應(yīng)當(dāng)要求權(quán)利人不反對“被使用的”姓名是其姓名;如果姓名權(quán)人反對或者否認(rèn)該姓名,表明其無意享受該權(quán)利,法律不應(yīng)越俎代庖地給予保護。因為權(quán)利的取得必須以具有取得權(quán)利的意思為條件;倘若權(quán)利人尚且不認(rèn)為是其權(quán)利,法律沒有必要強加權(quán)利。事實上,權(quán)利人主張權(quán)利本身即表明其認(rèn)可姓名的使用。“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認(rèn)定美國公民喬丹對其中文名稱并未提出異議或者反對,且業(yè)已許可耐克公司在中國進行商業(yè)化使用。因此,“喬丹”姓名在中國境內(nèi)客觀上對于美國公民喬丹所形成的“可識別性”、美國公民喬丹對該姓名的認(rèn)可以及事實上已有的商業(yè)化使用,構(gòu)成了美國公民喬丹主張商品化權(quán)益的完整基礎(chǔ),僅僅強調(diào)“被使用”是不夠的,更不宜放寬到不以使用為必要。
(三)兩種因素與道德評價和道義觀
“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突出了惡意和誠實信用,還特意在行政裁判中援引《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由此附加了濃厚的道德評判和道德譴責(zé)色彩。在再審判決作出之后,這些道德譴責(zé)式的裁判理由受到一些人的大肆渲染。但是該案在本質(zhì)上涉及商標(biāo)法上的在先權(quán)利和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究竟如何看待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中的法律、政策和道德問題,是一個重要而復(fù)雜的問題。
知識產(chǎn)權(quán)雖然是一種財產(chǎn)權(quán),但與一般財產(chǎn)權(quán)有所不同。知識產(chǎn)權(quán)畢竟具有濃厚的貿(mào)易和公共政策工具色彩,不適宜添加過多的世俗道德意蘊,尤其要警惕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的道德渲染和泛道德化。首先,財產(chǎn)權(quán)益尤其是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問題,不具有人格權(quán)保護的嚴(yán)格性和絕對性,商業(yè)利益的劃分問題不簡單等同于道德,無需附加太多的道德譴責(zé)色彩。其次,簡單地將知名人物姓名違法用作商標(biāo)認(rèn)定為侵害姓名權(quán),其保護即具有剛性,由此得出的結(jié)論可能違背權(quán)益本身的屬性。將他人姓名用于商標(biāo)畢竟是轉(zhuǎn)換性使用,即使是使用知名人物的姓名,如果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特定姓名與特定商業(yè)標(biāo)識建立了聯(lián)系,該商業(yè)標(biāo)識即具有自身的正當(dāng)性,可以形成姓名與他人商業(yè)標(biāo)識共存的局面,而不宜以姓名權(quán)為依據(jù)改變這種商業(yè)標(biāo)志上的聯(lián)系。尤其是“喬丹商標(biāo)案”涉及的既是中國的又是跨國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問題。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制度經(jīng)歷了外力推動和自主發(fā)展的漸進過程,其間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程度由低到高,對于其階段性保護狀況要歷史地看待和解釋,不能以今天的眼光簡單地審視過去。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發(fā)展與完善是中外利益博弈的過程,對于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格局應(yīng)當(dāng)給予尊重,不能簡單地以目前的高標(biāo)準(zhǔn)評判和改變當(dāng)時的保護狀況。對于因歷史原因產(chǎn)生的商業(yè)標(biāo)識正當(dāng)性問題,應(yīng)當(dāng)以符合歷史的道義觀進行解讀,尊重歷史顯然不是當(dāng)今的世俗道德問題,不能簡單地進行道德譴責(zé)和法律清算。 在其他系列案件中,美國公民喬丹撤銷相關(guān)喬丹商標(biāo)的主張未獲法院支持就體現(xiàn)了這種精神。
五、結(jié)語
根據(jù)現(xiàn)有相關(guān)立法格局和實際需要,我國對于姓名權(quán)與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應(yīng)該采取二元分立保護的法律模式。知名人物姓名的商品化使用具有獨特的財產(chǎn)價值,應(yīng)當(dāng)在姓名權(quán)之外另起爐灶考量和定位其權(quán)益屬性、保護范圍和程度等,將其作為獨立的商品化權(quán)益。而且,應(yīng)將其定位為民事利益,使其在保護范圍和程度上具有靈活性。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保護應(yīng)適度,一步到位式的、徹底的和不留余地的保護顯然過于激進,在利益衡量上是欠缺的和冒進的。知名人物商品化權(quán)是其在特定領(lǐng)域知名之后的溢出和邊際效應(yīng), 個人的知名經(jīng)常不是個人努力和才華的結(jié)果,并無證據(jù)證明保護此類權(quán)益有惠及整個社會的一般性經(jīng)濟效率。 因此,各國對于知名人物商品化權(quán)益的保護方式和程度不盡相同,但除美國以外,其他國家對于人格特征的商品化權(quán)益通常沒有太多的關(guān)注和討論,美國對此的重視保護與其特殊文化背景尤其是“有產(chǎn)階級狂熱的影響”直接相關(guān)。 我國的“喬丹商標(biāo)案”再審判決及《商標(biāo)授權(quán)確權(quán)司法解釋》對姓名的商品化權(quán)益已達到了如美國法上公開權(quán)那樣的充分保護程度,這多少與近年來我國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深受美國相關(guān)制度的影響有關(guān)。但無論如何,相關(guān)保護必須兼顧法律因素與政策因素,保護范圍的大小和程度高低更是一種政策問題,不能盲目追求保護水平上的高標(biāo)準(zhǔn),對此需要理性確立觀念和建構(gòu)具體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