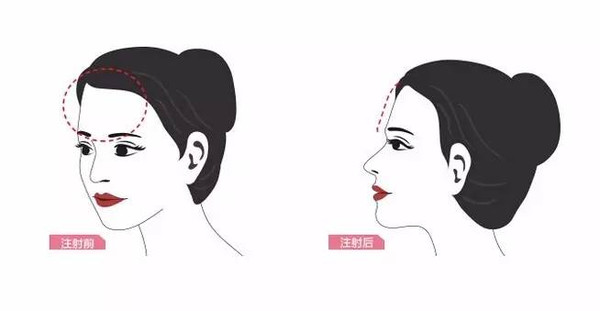近日,“黑馬”迪瑪希在《歌手》舞臺上翻唱維塔斯的歌曲被控侵權,雖然截至目前該事件前因后果并未明晰,不過其折射出的翻唱授權問題,再度引發公眾關注。
無論是綜藝節目還是音樂類演出,翻唱歌曲要獲得授權,可謂天經地義。而在國內,只要說到翻唱版權與授權,人們通常會第一時間想到一個名字:音著協。可在業內人士眼里,音著協已變成了“收錢”的代名詞。在版權維護方面,音著協到底扮演著什么角色,何以版權授權到現在還亂成一鍋粥?
亂象:版權授權無章可循
音著協,是中國音樂著作權協會的簡稱,成立于1992年,是由國家版權局和中國音樂家協會共同發起成立的中國大陸唯一的音樂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在我國,大多數音樂人都是音著協的會員,大部分歌曲的版權也就交由他們打理,少部分版權歸屬大型唱片公司或獨立音樂人自己運作。
由于音著協掌握大量版權,幾乎所有的電視節目或演出主辦方需要獲得歌曲授權時,都會先想到它。可問題出現了,早在2013年,《中國夢之聲》選手許明明參賽時演唱《我在人民廣場吃炸雞》,就引來原作者阿肆所屬公司摩登天空的不滿。雖然節目組表示已向音著協支付過版權費用,但摩登天空卻稱并沒有授權音著協代理版權業務。2015年,《中國好聲音》冠軍張磊也被指責在比賽和商演中,未經授權翻唱了民謠歌手馬頔的成名曲《南山南》。
就此問題,記者登錄了音著協的官方網站,卻只發現了使用音樂表演權,即在演唱會或音樂會上使用他人作品的授權許可標準,并未發現在電視節目中翻唱音樂作品的許可與收費標準,也沒有找到音著協所擁有版權的歌曲曲庫。隨后,記者多次致電音著協,工作人員始終表示相關負責人不在,無法回應。
奇聞:可用門票抵版權費
音著協在處理版權問題時語焉不詳,而當業內人士提起音著協的時候,他們通常的印象都是——收錢。
演出行業經常與音著協打交道,一位從業人士就曾在主辦演唱會時與他們有過交涉。“原創型歌手辦演出還好,如果非創作型歌手想在演唱會上翻唱其他人的曲目,就要得到授權。”據他介紹,關于使用音樂作品進行表演的使用費有一定之規,原則上是按使用的曲目數量、時長收費,與演唱會的票價和座位數也有關系。
“不過價格是可以談的。”他口中的“談”,指的就是不必一定按照規矩來,有討價還價的余地,“雙方覺得差不多了就行,一場在兩三萬元左右,一般不會超過五萬元。”不過有時,音著協的工作人員也會根據演出售票的緊俏程度,提出“用門票抵版權”,“如果特別火的、票賣得好的演出,就給他們一些票,賣得一般的演出,還是直接付錢。”
音樂人李志遇上的事更讓人哭笑不得。李志團隊經紀人遲斌回憶,李志在北京籌辦演唱會時,就有音著協的工作人員找上門來,稱李志要交翻唱的版權費。“可李志唱的都是著作權在自己手中的原創歌曲,根本不涉及翻唱授權啊。”聽遲斌這么說,對方又稱“李志是音著協的會員,所以要交錢”。“李志真不是。”遲斌非常無奈,“李志從未加入音著協,也從未把自己的原創版權授予他們管理,何來此說?”在遲斌的要求下,音著協工作人員當場查證,發現李志果真并未加入音著協,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管理:收益核算尚需健全
“理論上說,音著協作為保障音樂人權利的版權管理機構,在收取版權費時應有一定之規,不應像從事商業行為一樣議價。”業內評論人王毅認為,除了存在管理問題,沒有對版權信息進行數字化、系統化統計,也是病因所在,“版權曲庫不完善,有時甚至說不清一首歌的版權歸屬到底是誰,雙方也就將錯就錯地談價格。”
對著作權人來說,音樂版權收益鏈條的核算也存在漏洞。不少音樂人反映,在把歌曲版權交由音著協代理之后,音著協很少主動為他們維權,或聯系他們交付版稅,即便有,也是少得可憐。據了解,一些知名音樂人一年拿到的版稅僅在百元左右。
音樂人要想知道自己的歌在什么時候、哪個地點、被誰演唱或使用,這些具體信息也不透明。“李志之所以不愿加入音著協,就是因為加入之后,所有的版權和著作權交易,從定價到使用都可以不通過我們來執行。”遲斌補充道,“如果綜藝節目用了他的歌曲,他反而成了最后一個知道的。”
王毅認為,國外的一些管理經驗可以借鑒。“國外的音樂行業,內部分類很細致,搖滾、電音等每一種音樂類型都有各自的行業協會或聯盟管理版權,每一首歌、每一條詞曲的版權歸屬都有數據可查。”此外,國外也有專門的版權公司計算收益,管理體系很健全。“當然,這也與版權意識強有關。”王毅說,“國外還有嚴格的誠信記錄制度,一旦發現有侵權行為,侵權人以后貸款、出國都可能受到影響。代價提高了,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侵權行為的發生。”